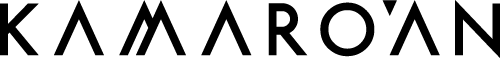物的交易、人的交流、靈的媒介-薯榔、檳榔
文/ Tipus
圖/ Badagaw、Tipus
資料整理/ Imay
幾年前曾在部落看過 ina Sumi (舒米・如妮阿姨)以藍染及薯榔煮染輪傘草裡的纖維,輪傘草的莖皮在日曬捲曲後會拿來做桌蓆,而輪傘草莖內纖維取下之後用薯榔煮染後,捻成繩也成為窗簾的一部分,而且纖維看起來更加穩固也不會毛躁。
有經薯榔煮染的輪傘草纖維製成的蓆子
地域盛產的交易貿易
薯榔尖、石筍尖、峰頭尖為「平溪三尖」。
《纖維實踐》寫到:「這個地區因為早期盛產薯榔,早在嘉慶道光年間就以此命名,居住在這裡的先民,除了從事礦業,另一方面也採集山林的作物販售,他們循著山林的路徑尋找薯榔,販售後換取生活所需,然後在山腳下形成自己的生活聚落-薯榔村。」
早期臺灣沿海漁民習以薯榔染漁網,使其纖維各為強韌,主要是薯榔有單寧酸及膠質。以漁獵維生的阿美族、達悟族也會利用薯榔染漁網,讓漁網耐用與防腐(花蓮縣富里鄉阿美族、臺東縣臺東市阿美族、臺東縣蘭嶼鄉達悟族、臺東縣池上鄉阿美族)。
而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族多以染製在線材、背袋、衣服、棉被上,也會採集販售給漁港的漢人(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、臺東縣卑南鄉魯凱族、臺東縣金峰鄉魯凱、排灣、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)。參考來源:《拾回被遺忘的智慧-原住民植物染料薯榔應用之研究》
薯榔則是台灣早期清領與日治時期的貿易商品,主要銷往中國及東南亞,甚至在南投竹山鎮山區要有薯榔採集許可證,且只有秋冬才能進行薯榔挖掘。直至 1950 年代尼龍纖維漁網傳入取代薯榔漁網。
臺灣原住民早期薯榔都以槌染為主,布農族與太魯閣族以先染纖維後織布;阿美族則多以織布後才染薯榔,也會放入泥土內好幾個月媒染,讓顏色更深及固色。
槌染的薯榔
萃取薯榔染液階段
由上而下:苧麻布以薯榔鐵媒染樣布、棉麻布以薯榔鐵媒染的樣布、苧麻布薯榔石灰媒染樣布、棉麻布以薯榔石灰媒染的樣布
薯榔鞣製皮革的工藝消失
特別的是,薯榔鞣製皮革的技術。
在《拾回被遺忘的智慧》紀錄到:「臺東市卑南族染製山羌皮衣,軟而耐用。」《大地之華》裡也寫:「以薯榔鞣製皮革曾經也有不小的產量。」,同時也在《纖維實踐》裡讀到,「薯榔作為染料使用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宋代,主要揉製皮革,真正大量用於染製布料與漁網,是始於明朝。」,但現代以薯榔鞣製皮革的工藝,也已不見工序紀錄及實品了。
紅色素及兒茶精的檳榔
曾看過一個故事,「一位老奶奶食用檳榔但檳榔過老,老奶奶將檳榔槌打後食用,在旁的小孩子學老奶奶將檳榔放進布袋槌打,布袋就染色了!」
《大地之華》提到:「過熟檳榔皆是良好的染色材料,我們可以不費文地的撿拾利用。...嚼食般大小的檳榔果亦可染色,其色素主要在於核仁之中,所以煎煮前,嫩者必須以刀具切成數辦,老硬者必須以重物擊碎,才好將色素萃取出來。...檳榔富含檳榔紅色素及兒茶金精,染色時應勤加攪動,以免局部迅速氧化而產生染斑。」
曾經在《花蓮太巴塱部落的工藝社造》論文中看到是以「檳榔根搗碎後可用於染色」,其技法在部落中也很少見了。所以,我們推測,早期原住民族少使用檳榔作為染色材料,是移民時期帶進來的技術,加上薯榔當時的實用度較高,檳榔有其他的用途,則使用於染色工藝才不見普及。
《大地之華》:「日本鎌倉時代已有使用紀錄,《當世染物鑑》、《鄙事記》等書中皆有『檳榔子染』之記載,當時檳榔子主要是和石榴、五倍子等物合用,並以藍靛打底,加上鐵媒染後可以得到黑色。」及檳榔煮染的特性:「檳榔富含檳榔紅色素吉兒茶精,染色時應勤加攪動,以免局部迅速氧化而產生染斑。」
萃取檳榔染液
檳榔籽萃取染液乾燥後
照片第三張由上而下:有苧麻布、棉麻布與石灰媒染的樣布
檳榔、荖葉與石灰的愛情故事
而檳榔,臺灣的特色水果,在《看不見的雨林-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》在「是誰的文化資產-臺灣熱帶植物引進史」一章有提到,檳榔來自東南亞,與檳榔一起食用的荖葉也可能是原住民在航海時代所引進臺灣。
紅唇與黑齒:檳榔文化特展提到:「檳榔原產於馬來西亞、印尼一帶。分布區域涵蓋中國、東南亞、南亞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島嶼和半島。台灣則以南投、嘉義、屏東及花蓮等地最多。」
蘭嶼達悟族,有檳榔與荖藤(荖葉)及石灰的故事,內容與阿美族的傳說故事雷同,都是象徵愛情的元素。
嫩青的檳榔果實食用時澀味重,早期會用來潔牙,加入貝灰後檳榔會產生色素但在食用時會減少澀味,也會有提神的效果。劉炯錫老師也說過,排灣族會將果實穿洞綁線當奶嘴使用。
檳榔與人的社交文化
結實累累的檳榔在婚嫁中有祝福新人早生貴子、多子多孫祝福家族人丁興旺之意;在阿美族的部落中祭儀時,女子給男子檳榔皆有表達情意,各部落不同細節也略有不同,有些部落男子拿到後馬上吃代表男子也有情意,若放入 alofo’ 佩袋中則代表男子無意。
同樣的在排灣族、魯凱族、卑南族中,檳榔也都有情意傳遞的意思。
在阿美族的部落中,在路上遇到友人也會拿給檳榔表達禮貌;更有在人與人爭吵之後以檳榔表達欠意及和解的媒介。
《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》也有提到,韓愈到廣東省擔任刺史,因南方氣候病倒,當地居民贈送檳榔食用後則痊癒,民間因受韓愈照顧間廟祭拜,有「檳榔神」之稱。而柳宗元、朱熹、劉伯溫、等人都有吃檳榔以消南方瘴癘之氣。另外,晉朝稽含著作《南方草木狀》也提到檳榔作為遇上貴客,會送上檳榔。」余文儀(1774年)《續修臺灣府誌》李也寫到婚禮以檳榔及荖葉為聘禮。
Akac 陳豪毅家屋裡的 fakar 備有檳榔食用
檳榔-人與靈的媒介
檳榔在原住民社會中,也是族人與祖先、神靈溝通的媒介。
阿美族婚的檳榔是宗教祭祀的祭品;西拉雅族會將檳榔剖半作為筊杯;南王卑南族由祭師將陶珠放入檳榔,向祖先進行祈福可與祖先溝通。馬卡道驅逐驅趕邪靈,檳榔也是必備的道具。
阿美族永安部落祭儀祭祀用的檳榔、荖葉、米酒
太巴塱部落 Kakita’an 家屋祭桌上的檳榔及米酒
薯榔作為經濟作物貿易到中國及東南亞國家;檳榔在原住民的航海時代帶入臺灣。兩者相同的是不同族群使用方式細節各有不同,但目的卻大同小異。薯榔作為植物纖維的強化與防腐,並在臺灣島內形成供給與需求的交易與交換;檳榔作為禮儀及祭祀的祭品,也是人與人交流的重要媒介,在生活中有極重要的角色。
兩種植物皆是紅色調自然草木染的染材,原來在早期就已穿梭在各族群的日常生活中,不同時代的意義及精神都是生活中積累的文化特徵,跨時空多元角度的認識你我之間的文化交集。